飞机着陆一小时了,仍不见影子,让我捏了把汗。美国国会刚通过的限制移民的法案,由电脑网络输进所有机场移民官员的大脑,映在脸上,肯定雪上加霜。老刘终于从自动门探出头来。八年没见,他明显苍老了,让我想起他父亲。他穿的竟是那件七十年代就穿上的土黄色羽绒服,领子很脏,袖口磨破,好像有意嘲笑由林同炎先生设计的旧金山国际机场,旅客们正由此飞向未来。
我们开车回到过去。他一上车就要抽烟。无奈,只好开窗,烟缕在风中急剧抖动。屈指一算,我们认识已有二十五年了。一九七二年春天,中学同学唐晓峰神秘地告诉我,他的邻居是地下艺术团体“先锋派”的“联络副官”,这两个称号具有同样的吸引力。老刘在工厂当钳工,但文质彬彬,像个旧时代的文人。他刚从大狱里放出来,因反动言论关了三年。有幸和不少文化名人关在一起,关出不少学问和见识。他仍像个犯人,缩在双层铺和小书桌之间,给我讲狱中的故事,他立志要写出来。经他介绍,我认识了“先锋派”的“猴子”——也就是后来的芒克,又通过“猴子”认识了彭刚,其实“先锋派”也就这两位,再加上联络副官,三人行。
第二天,老刘系上围裙,麻利地操刀掌勺,给我们做饭。他在波兰开了家中国饭馆,生意兴隆。一九九O年夏天,他无法忍受国内的沉闷气氛,去了匈牙利,混了半年,又转战波兰。诗人一平,跟我讲起在波兰的奇遇。街上问路,他正好问到一家中国饭馆。有人应声,从地下推开扇窗户,爬了出来,满脸烟熏火燎,露出白牙——正是老刘。先有免费打工的铺垫,才有后来的发展。他攒钱,在大学区盘下家小馆子,当起厨师、红白案、采购、会计,兼老板。
老刘的变化让我目瞪口呆。八十年代,我们这帮人里,顶数他日子过得滋润。他为香港中新社到西藏拍纪录片,赚些外快,购置了电器和罗马尼亚家具。要说不在钱多少,而是一种态度:人生难得几日闲。他经常备上酒菜,请朋友聚聚。他说话和时代节奏成正比。起先慢条斯理;商业浪潮来了,带有间歇性停顿;他卷起铺盖上路了。
和老刘相比,实在惭愧。在国外,除了靠奖学金,靠母语在学校混混,我还能干什么?所谓先生存,后发展。文人自己种稻做饭,自然不必“为五斗米折腰”。对美国,老刘最初的反应是谨慎的。他仔细比较价钱,从生姜到汽车;他收集饭馆的菜单,留意报纸上的分类广告。我终于从他眼睛里看到了什么。我也从欧洲过来,知道一个中国人在另一古老文化中的失语状态,知道那随经济浮动的排外情绪,也知道新大陆呈现的种种幻象。老刘想和他的美国梦一起留下,但美国移民局的答复是:您留下梦,走人。
七十年代,我和老刘常结伴出游,去过白洋淀、五台山等地,没想到如今可走远了,远得望不到家、回不成家或干脆不想回家了。七五年秋天,我和父亲吵架,一怒之下和老刘上了五台山。那颓败的庙宇和稀疏的松柏沐浴在夕阳中,呈凄凉之美。我们认识不少和尚,多是农家出身,质朴可亲。有位尼姑是四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为何出家?必有一段隐情才是。
在昏暗的光线下,她满脸褶皱,目光清澈。谈得投缘,我们把一本任继愈关于佛家思想的书送给她。最后钱用光了,我们经大同扒火车回北京。快到北京时,我们为在哪儿跳车吵了起来。老刘执意要在远郊的小站下,我认为目标太大。俩人脸憋得通红,怒目相视。最后还是在北京站下车,翻墙逃脱。拐进前门一家澡堂子,泡了个热水澡,躺在铺板上,抽烟,望着天窗,我们才开始说话。
话说回来了,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老刘的两次婚姻都失败了。现任妻子和他在一起开饭馆,仅仅因为在国外手续复杂,离婚一拖再拖,拖得两人都没脾气,只能将就。情人节快到了,我女儿偷偷问我:“为什么刘叔叔买了两张情人卡?”我怎么解释?一张给妻子,出于习俗和生活惯性,另一张是给波兰房东的女儿,那是真情。老刘请我把他的题词译成英文,再抄在情人卡上,但他连情人的名字都拼不准。我为他感到悲哀:除了有限的波兰饭馆用语外,他用什么来表达?但这毕竟是他仅有的阳光,在烟熏火燎的异地他乡。
老刘生性温和,知书达理。按一平的话来说,他是个毫无侵略性的人,在此伤天害理的年月实属少见。祖上是河北农民,若无革命,他很可能是个乡下秀才,度过平静而儒雅的一生,时代改变了脸,让他入大狱,做苦工,险些病死在铁栏杆后面。而这狱中经历成了他的命运。好不容易消停两天吧,逼得他远离故土,沿成吉思汗的路线给远房亲戚们生火做饭。母亲病重,那些穷亲戚在路条上百般刁难,竟没让他回去见上一面。
直到最后一刻,母亲仍盯着门口。
“我现在是赎身。”老刘酒后伸出指头,“十万!只要攒够十万美元,就告老还乡了。”他脸色红润,一扫刚来时的晦气。挣钱赎身,回家,回乡下,买房置地,读书写作,过老秀才的生活。这倒是他一辈子理想。自打认识,他就一直叨唠这事。可何为以后?
那天乘游船在旧金山湾兜风,金门大桥像把尺子在我们头上翻转,好像在测量我们有限的一生。我们在它下面合影,为二十五年的友谊,其实二十五年只是它最小的刻度。
就在老刘到的前两天,我女儿告诉我,有个叫彭刚的来电话。莫非是那个二十五年前“先锋派”的彭刚?果然,他来美国多年,前两年搬到圣荷西(San Jose),离我这儿不远。我给他打电话,说有人想跟他聊聊。老刘接过电话,自报姓名,悠悠然。彭刚惊呼见鬼,风驰电掣而来,拎着香槟和啤酒。那聊法有如登山,对年轻的不算什么,上了岁数就明显感到吃力。日薄西山时,不免感叹:众人星散,看来“联络副官”这些年有点儿玩忽职守。
老刘要回去了。那边饭馆告急,加上签证也到期了。临走,我陪他去采购。他买的都是饭馆所需,大到蒸锅,小到姜蒜,塞满一个大纸箱。我打电话为他订位时,发现由于班机衔接不巧,他得在巴黎机场待整整一昼夜。我拉他去法国领事馆办过境签证,不肯,他要为赎身省钱。结果在机场遇到麻烦。柜台后面漂亮的小姐皱着眉头,一边翻着护照,一边打量着大纸箱和那身七十年代的羽绒服,她坚持老刘必须得办法国签证。好说歹说,又找来上级,才放行。
别后,我一天都心不在焉。在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正当搬运工人倒腾那个大纸箱时,老刘缩在柱子后面,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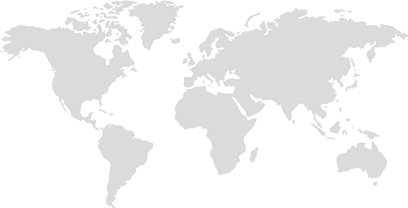






 汽车
汽车




 电话:0591-87851720
电话:0591-87851720
 传真:0591-87851720
传真:0591-87851720
 邮箱:minswx@163.com
邮箱:minswx@163.com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数字内容产业园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数字内容产业园
 法律顾问:福建宏飞律师事务所 吴跃华 主任律师
法律顾问:福建宏飞律师事务所 吴跃华 主任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