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民国女人》,作者:王开林,出版:东方出版社
阮玲玉年少孟浪,跟张达民同居等于一个猛子扎进了河泥。结婚不像结婚,恋爱不像恋爱,这给她的人生预埋了一颗结结实实的悲剧种子。狂蜂浪蝶摧花辣手一旦向阮玲玉伸来,她就从此难以摆脱。张达民若肯安分守己,与阮玲玉恩爱相伴,哪怕他平庸一点,阮玲玉也不会怎样埋汰他。可他是那种挥金似土的魔术师,尽管继承了多达十余万元的丰厚遗产,但他嫖赌逍遥抽鸦片,样样化钱,没几年光景就囊空如洗。
阮玲玉不慎将终身托付给一个混世魔王,后果不堪设想。但她还在盼望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奇迹。为了奉养母亲,同时担心着前途,她决定谋求经济上的独立。也算天从人愿,阮玲玉进入电影界后,以其过人的艺术悟性和表演天赋站稳脚跟,并且迅速窜红。
张达民荡空遗产后,阮玲玉成为他唯一的摇钱树,他以做生意为名,欠下高利贷,然后花言巧语骗光阮玲玉的积蓄,去赌桌上寻求一掷千金的刺激。久而久之,阮玲玉对嗜赌如狂的张达民有所防备。当她不肯爽爽快快给钱时,张达民就使出“撒手锏”,拿阮母出气,不由分说,照准阮母的脸上就是“啪啪啪”几记耳光。阮玲玉是孝女,眼看母亲挨打,脸都气得煞白了,身子抖个不停,她终于认清张达民的狰狞面目,原本期望他能改邪归正的那份热切的心愿也就冷却下来。
阮玲玉是觉悟日增的新女性,她对张达民这号赌棍、败家子、鸦片烟鬼不可能有良好的观感,也不可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因为性格软弱,她也很难拿出“蝮蛇一螫手,壮士急解腕”的决心。再说,她看重名誉,生怕授人以柄,自己私生活上的不快会被那些闻腥起舞的苍蝇(黄色小报的记者)逮住,七炒八炒变成街谈巷议的材料。阮玲玉见过不少同行被黄色小报污损之后再难翻身,她可不想步其后尘。于是,阮玲玉能忍则忍,对张达民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任由他吃软饭吃得心旷神怡,做无赖做得肆无忌惮。
1931年春天,出道五年的阮玲玉已是“联华”的台柱子,其名头与“明星”影后胡蝶并驾齐驱,片酬也提高到当时的一流水准。她有心过一种更独立更自主的生活,就从张达民名下的祖屋搬出去,住到上海法租界的华格臬路大胜胡同。眼看羽翼丰盈的天鹅要飞走,张达民心里可不是滋味,他仍一如既往厚着脸皮找阮玲玉要钱,若不能得逞,他就寻到摄影棚里大吵大闹,让阮玲玉下不来台。
张达民扑钱的花招很多,强行索取不奏效,他就找些带刺的题材去要挟阮玲玉,比如说,他将报纸上刊登的“电影明星胡蝶诉未婚夫林雪怀无故解约案今日开庭,千余旁听者挤破法院门厅”的新闻第一时间快递给阮玲玉。不用说,这是借力打力,他有意让她思忖思忖,掂量掂量。阮玲玉细读这篇报道,方知胡蝶在法庭上经历了种种难堪,法官和林雪怀的律师提出了一大堆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等于撕下内衣给人瞧,胡蝶不得不—一作答,法庭内的旁听者乐得偷窥大明星的隐私,简直比看电影还要开心,还要过瘾,时不时地发一阵笑,起几下哄,逗惹得黑袍法官用法棰猛敲案桌,大呼肃静。阮玲玉设身处地想,换了她,窘都会窘死,羞都会羞死,哪能由着法官和对方的律师那样折腾与摆布?张达民在一旁察言观色,又火上浇油地说:
“胡蝶的情变风波已原原本本上了报纸,那才叫绝呢,不过,你十六岁就跟我上床的故事完全可以与它比个高下。要不要我将详细经过讲给那些黄色小报的记者听听?我肯定,你的这段情史准能卖个辣价钱。”
张达民此言一出,阮玲玉顿时花容失色。
当年,“上床故事”属于爆炸级的“猛料”,若放在当今网络时代,简直不算一回事。车模兽兽的三段性爱视频被某男发送到互联网上,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真刀真枪地干”,“极情极性地做”,绝对是限制级的。结果如何?兽兽不仅没有被羞辱的唾沫淹死,反而更频繁地抛头露面,身价倍增,大红大紫。这就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阮玲玉深知,一个无行小人若见利忘义,绝对是什么丑事、坏事都做得出来的,她立刻制止张达民:
“你千万别胡闹,这样做会毁了我的前途。”
“我也不想翻旧账,可是一个铜板就能憋死英雄好汉……”
说到底,张达民除了要钱还是要钱,这回,他的威胁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阮玲玉答应满足他的要求,并且设法为他谋得一份体面的差事。她天真地认为,这家伙有薪水可拿,不会再像一条饥饿的癞皮狗老来纠缠了。没多久,“联华”的董事长罗明信不看僧面看佛面,聘用张达民为光华戏院的经理,月薪一百二十元。在当年,这份收入并不低,联华公司一般演职员的薪水每个月才不过四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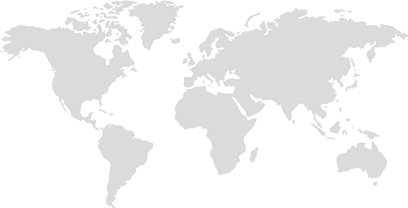






 汽车
汽车




 电话:0591-87851720
电话:0591-87851720
 传真:0591-87851720
传真:0591-87851720
 邮箱:minswx@163.com
邮箱:minswx@163.com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数字内容产业园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数字内容产业园
 法律顾问:福建宏飞律师事务所 吴跃华 主任律师
法律顾问:福建宏飞律师事务所 吴跃华 主任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