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业余时间里,Sven Laumer会给巴伐利亚最高级别的足球联赛担当裁判。几年前,他注意到好几名球员不再登陆Facebook,这使得他很难在该平台上组织活动。他很郁闷,而身为研究信息系统的教授,他也对此非常有兴趣。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不再玩Facebook了呢?社会科学家可曾说过社交网络是个好东西呢。
「那段时期,社交网络研究的主流观念认为Facebook是个有正面作用的地方,是个充满幸福感的地方,能让你找到乐子,感到愉悦,能和朋友聊天,感到趣意,找到认同感。」说这话的是瑞士伯尔尼大学的信息系统研究员Hanna Krasnova。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也表明我们从社交媒体获得的社会资本也是我们成功的要素,不论大小。这些虚拟的联系帮助我们获得工作、信息、情感支持和日常帮助。Laumer是德国奥托·费里德里希大学的助理教授,他认为每个人都热衷于社交媒体。他知道有些研究员会有高新技术紧张症,会因为有缺陷的接口或复杂的处理过程而在工作中表现出来。但这并不适用于Facebook,因为它用起来非常简单。而有些事似乎会让人压力过大。Laumer说:「我们认为社交媒体表现出一种新现象。」
Facebook的产品「新闻递送」并非娱乐,它似乎就像是提出一大堆要求的清单。给我鼓鼓劲吧。安慰一下我吧。祝我生日快乐呀。给我施舍点投资啊。
通过探测采访、调查、纵向研究和实验,研究员们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Facebook、推特、Instagram、Snapchat以及同类型的平台并不是充满成功与欢乐的地方,相反,却是黑暗的、对抗的、以及原始的——不是什么魔幻王国,而是诡异的小房子。研究员们认为,这些平台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我们这一物种最本质的性格之一:社交天性。所以毫不稀奇会出现非预期结果。
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Ethan Kross说到:「没人会特意构造出一些东西来让人们感到开心或难过,但是我们想知道,这些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并且如何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一个结论是使用Facebook会让你感到有点伤心——这种现象很出名,叫做「Facebook抑郁」。Kross和他的同事在2013年对Facebook进行研究时,每天5次向82位Facebook用户(大部分都是密歇根大学本科生)发信息询问他们用了多久的Facebook了,感受如何。Kross说道:「我们发现,在一段时间内使用Facebook越多,这一时期心情变差程度就越厉害。」
坏联系:通过短信与家人朋友进行沟通使人丧失人性。
为什么?Laumer和他的同事们注意到,对于某些人来说,Facebook的产品新闻递送并非娱乐,它似乎就像是提出一大堆要求的清单。「给我鼓鼓劲吧。安慰一下我吧。祝我生日快乐呀。给我施舍点投资啊。快给我的新照片点赞。快看我Nautilus的新功能。」社交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放大了每个用户的需求。这些有需求的人不需要一对一的提出需求;就像是散弹枪一样,一对多的碰一声命中多人。毫无疑问人们会因为他们而感到压力。而压力是当人们感到他们没有资源或能力应对某些潜在威胁时而产生的——这种情况下,Laumer将这种威胁称之为「过度社交」。
讽刺地是,过度社交是某些研究员所认为的社交媒体最积极方面之一——社交共享的对立面。将自己的问题在网络上和其他人共享能够减少很多方面的压力,从日常压力到生活转型,到自然灾害,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社会医学家Shelia Cotten如此说道。她在某项研究中发现Internet的使用能让年龄较大的美国人减少孤独感。「有一大堆的让你能进行交流的社交活动会对健康安乐带来非常有益的影响,能够帮助减缓压力。」然而问题在于,你的压力减少了,却把压力转移给了别人。
罗格斯大学的社会学家Keith Hampton为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进行了一些社交媒体调研,他将这种「二手压力」称为关怀的代价。他认为,女性的这一代价要比男性更高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因为不论线上还是线下,她们都承担更多照顾家庭和朋友的负担。他说:「当你意识到某些不好的事发生在你认识的某人身上,这虽然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压力,但也让你能给予他们社会支持,表达你们的同情心。」
但并非所有的朋友都会创造等价的在线价值。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无限制的添加联系人——包括那些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怎么或压根不会见到的人。Hampton说:「这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持久关系。」Laumer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过度社交更可能对那些拥有更多仅Facebook好友的人造成的影响更大。
这是有道理的。在1990年代,人类学家Robin Dunbar宣称人类一段时期内有时间和能力维持100-200位的友情关系。在最近的一项涉及170万用户的研究中,Dunbar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推特用户维持的「稳定社会关系」数目大抵持平。但如果我们在推特或Facebook上有150位我们会时常联系的好友,而他们全都经常表现出需要社会支持的话,我们所接触到的各种要求就比我们祖先接触到的多得多。那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怎么办呢?很多不知所措的用户就会干脆全部退出。Laumer说道:「过度社交会造成强烈的疲惫不堪。」
Facebook、Instagram和同类平台并不是充满成功与欢乐的地方,相反,却是黑暗的、对抗的、以及原始的——不是什么魔幻王国,而是诡异的小房子。
最重要的是,研究证实每个使用者都会遇到的:朋友们倾向于发出那些让他们看上去不错的东西。在一部波特兰讽刺短剧中,Fred Armisen的角色在一次去往意大利的周末中戴上了他的新情人,他们就在酒店里睡过了整个假期,痛苦地结束了旅程。而早先他们发出了一堆笑意满满看上去很是开心的照片。当他回到家,看到他的好友(Carrie Brownstein)在浏览这些照片,并向他的这趟旅行表示祝贺时,他告诉他:「因特网上每个人都并非像你所想的那样有一段好时光。」而她回复到:「我猜大家都只是把悲伤藏了起来。」
这是实话,即使人们并没有藏起悲伤,而是发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傻事或负面事情,我们可能也不会注意。人们会自动停留在高社会地位的人身上——特别是看起来有吸引力或富有的人 (比如卡戴珊)。Charlotte Blease是研究抑郁症的认知科学家,她认为社会地位是社交媒体抑郁症的根源。在一篇名为「太多『好友』,太少『赞』?进化心理学和Facebook抑郁症」的论文中,利兹大学和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员Blease将我们祖辈的环境视为一种解释。
Blease告诉我们,有一种对于抑郁症的进化解释是社会竞争理论。该理论认为抑郁症是一种自适应行为——孤僻、低姿态、低自尊感——能够使我们的祖先从敌对的社会成员前全身而退,是一种能够不遭受物理损伤就控制其他人的暗示行为。换句话说,抑郁,活着。Blease说:「这就像是一种缩小冲突范围的战略,类似把手放在空中的无意识反应。」
这种自适应行为——假意顺从、放低社会地位——一直如影随形。在现代的环境下,当我们感到我们被那些高社会地位或高声望的人超过时,就会触发这种机制。Blease说:「我们被这样的人所吸引,而之后我们又会一直觉得『跟他们相比,我就是个失败者。』」
当然社会比较也会让我们变得面目可憎。从进化论的角度讲,嫉妒,就像轻度抑郁一样,可能也是自适应的——它促进我们向别人学习,并设定更高的目标。Krasnova表示嫉妒也令人痛苦,使得难以对它进行研究。她说:「这是种非常不好的感觉,所以我们通常并不愿意承认我们嫉妒了——不向任何人承认我们感到了嫉妒,甚至连自己都不承认。有时候情绪压抑的如此厉害,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何感觉,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如此生气或如此悲伤,为什么如此恼怒或如此压抑。」
状态更新:在获取注意力方面,普通生活几乎无法和社交媒体比,尤其是社交媒体能够提供源源不断地高社会地位人的魅力信息。
当Krasnova和她的同事们向357名试验对象——大部分来自于她工作的地方,德国——询问在最近使用Facebook后感觉如何时,只有1.2%表示他们感到嫉妒。因此她改变措辞问到:「很多用户报告称在使用Facebook后感到沮丧和力竭,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呢?」在这种情况下,最普遍(29.6%)的回复是嫉妒。她表示嫉妒不仅是使用Facebook的人的普遍情绪,它还会蔓延。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希望受到邀请的派对,同事获得的奖金等等。在Paula Hawkin的心理惊悚片《列车上的女孩》中,主演Rachel Watson在登陆Facebook并看到前夫宣布生子的消息时仍然感到痛苦。
Krasnova表示人们发现一种能够暂时从嫉妒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方法就是多发他们自己的东西。但她警告,这会在社交网络上造成「嫉妒螺旋」的威胁。「用户身处正面内容中,他们就发出更正面的东西,而看到他们发出内容的人发出更加正面的东西,以此类推。最终Facebook的世界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
然而,在最近的文学作品中,可能最具启发的发现就是人们在不发东西时,对自己所造成的伤害最大。这个脱离现实的世界并没有将我们和朋友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反而增加了距离。MIT心理学家Sherry Turkle在她的《开拓对话》一书中谈到了「表达真实自我的欲望和表现最佳自我的压力之间」的矛盾。但研究表明事实上在我们发帖时,我们并没有表现出最佳的、最富同情心的自我,虽然我们自以为如此。芝加哥大学行为科学家Nicholas Epley让商学院学生做了几场不同形式的电梯演讲。当学生们感觉他们在有稿演讲表现得更好时,评估专家觉得他们在脱口演讲时表现得更好。
这同样适用于Facebook:最近一项研究与Epley的结果有类似的结果,朋友们认为我们本人比照片中要好。「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的数据表明文本正在让人失去人性——也就是说,它无法像声音一样表现人类独特的品质、思想和感觉。」
Facebook的嫉妒螺旋甚至能让我们反目成仇。Krasnova说道:「我们的研究清楚表明在很多情况下,自我推销信息被视为消极的,并被解释为非常苛刻的。」部分研究员们警告,随着我们管理在线图片的时间愈长,我们会愈发自恋——与此同时,更加缺乏同情心。Epley说:「几乎没有数据能够说明自恋是件好事。从短期看,相当不错,但从长期看,对你们的关系并无好处。」
在今年出版的一项研究中,Kross和他的同事们,包括第一作者荷兰马斯垂克大学的心理学家Philippe Verduyn邀请了密歇根大学84位本科生来到实验室,其中一半积极使用Facebook,而另一半则消极使用。Verduyn解释道,积极用户要「发状态更新、聊天、回复评论,而消极用户只浏览新闻递送,看看图片和状态更新。」几小时后,积极用户没啥变化,而消极用户感到情绪有些低落。Kross说:「当你只是消极地使用Facebook时,你更容易感到嫉妒,最后会使人们感到更糟。」
一方面,这一发现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有方法能够摆脱Facebook抑郁情绪,而且还无需放弃社交媒体带来的益处:更活跃,更积极。另一方面,很少人能利用上述空子。
Verduyn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实验对象约有50%更有可能消极使用Facebook。这不仅限于千禧一代。市场调查公司Global Web Index报道称在2014年仅有52%的Facebook用户是积极使用者,跟2012年的70%相比有所下降。人们为何如此消极尚不明确。可能因为浏览比发帖要简单得多,但对Facebook黑暗面的其他研究表明人们可能是担心无意识的侮辱了某人、人际关系或工作面临风险、或者只是看上去像一个浪费时间的失败者。每一条发文都有可能公开羞辱了别人。不管原因如何,Kross说:「人们使用社交媒体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以一种潜意识有害的方式在使用。」——也就是,消极。幸运的是,社交网络研究是发现能够迅速得到实践验证的科学领域。研究可能揭示出有益和有害的行为,而不是简单地一分为消极和积极,同样也向不同的用户组——不同文化、不同年龄段、不同心理素质的人——阐明相应结果。科学家们仍然没有研究清楚社交媒体技术是如何影响人类天性的,但「希望在于,通过确定使人感到更糟的机制,我们能够开始想出一些方案,找到一种乐观的方式来与技术进行互动。」Kross说道。
某些Facebook的功能也有助于研究。在2011年,网站引进了「好友列表」功能,使我们能够限制我们的社会支持需求,仅将这些需求展现给我们认为最有可能关心这些的人,从而使其他联系人能够免除过度社交。2013年,我们有了「取关」功能,能让我们减少过度社交和嫉妒。2014年的「附近好友」和2015年的「视频通话」功能能够增加面对面的互动,而在Kross的研究中,面对面互动能够改善情绪。很快,预期的「互动」按钮——用来替代「点赞」按钮,包括「喜欢」,「不错」,「悲伤」——可能会给积极行为带来更多选择。
然而我们所希望的最重要的功能可能是用户固有的,而非技术提供的,即同情。人类文明的卓越成就,就是每一天人们都会克制超越别人的本能,只为了建立有意义、有价值的关系。然而在网络,那些看上去无害的「无滤镜」旅行照,完美的「我起床的样子」自拍照,以及无情的看似积极的「谦虚装逼」,我们不经意地让我们的朋友自感失败,并为「嫉妒螺旋」添了一把力,而这会使我们自己陷入险境。对于社交媒体黑暗面的研究正在逐步壮大,这使我们有机会来建立一种新社交媒体礼仪,让我们能将Facebook世界与现实世界重新联系起来,能改善真正的友谊,充满关怀与好处。我们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并非因为它使我们的压力减少了,而是因为某些压力值得拥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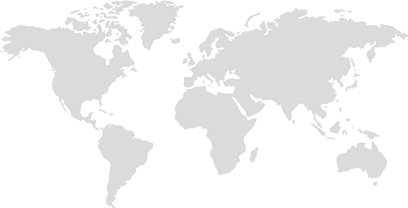






 汽车
汽车




 电话:0591-87851720
电话:0591-87851720
 传真:0591-87851720
传真:0591-87851720
 邮箱:minswx@163.com
邮箱:minswx@163.com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数字内容产业园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数字内容产业园
 法律顾问:福建宏飞律师事务所 吴跃华 主任律师
法律顾问:福建宏飞律师事务所 吴跃华 主任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