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商杂志-闽商网讯(邹挺超)1291年冬末,一位威尼斯商人来到泉州,他如是描绘刺桐给他的印象:
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他还谈到,这里风光秀丽,居民崇信佛教,一切生产必需品都非常丰富,一个威尼斯银币就能买到八个瓷杯。
这位商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的时代过去之后700多年,1997年,在荷兰莱顿召开的一次主题为“宋元时期泉州地区的海上贸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所集结的论文集标题是The Emporium of the World,将宋元时期的泉州称为“世界的货舱”。
尽管泉州的海外贸易兴起于唐,但是,南宋以至元末的两个半世纪,才是泉州海外贸易最兴盛的年代。那一时期的泉州,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的货舱”。
崛起之路
泉州的兴起,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的良好条件。
一方面,福建人自古以来就是擅长造船出海,海路交通发达。《山海经》中著名的那句“闽在海中”,以及三国时期吴国在福建设立造船基地等事迹,都说明福建海外交通的累积。
另一方面,泉州海外贸易逐渐崛起的时代,中国正是大唐帝国统治时期,对于与外国贸易往来,持鼓励态度。从国际上说,那时罗马帝国衰微,海运中心东移到波斯湾,此后,阿拉伯势力崛起,东起中国、西到非洲东海岸的海上交通,就此以波斯湾为中心连成一片。
从海上交通的形势上看,从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到东南亚,再进入中国南海,最容易看见的陆地,便是广东和福建。而福建又恰恰位于外国船只进入中国的门户——广州,以及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的中点,在海运上作为中转站的条件十分良好。
这一切,都为泉州在中唐以后成为中西“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奠定了基础。五代十国时期,闽国割据福建,又鼓励海外贸易,招揽外国商人。在割据时期,原本需要通过明州(宁波)等地中转的航线,变成直航,当时王氏政权都是直接前往山东,由此登陆向中原入贡,这直接促成了泉州与日本、朝鲜半岛的直接往来。另一方面,原本需要经广州中转的南洋贸易,也因此而转向直航。这对于泉州的影响更为深远。
经过五代十国时期,尤其是闽国时期的发展,到了北宋初,泉州的对外贸易已经十分发达。宋仁宗时代曾经两次知泉州的蔡襄,在其《荔枝谱》中就说,福建荔枝“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求、大食之属,莫不爱好”。
那一时期,泉州人还在中国与高丽的贸易上十分活跃。有学者曾经根据高丽史料统计过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至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的266年间,宋朝商人赴高丽的数据,在总数5000多人中,商人籍贯以泉州和明州为最多。明州是当时对高丽贸易的官方正口,后来还设立市舶司专门负责,人数多不出奇,但泉州商人之多,却也说明泉州商人对宋与高丽之间的贸易的专擅。
有意思的是,苏东坡曾经专门就此写过一封奏折(《论高丽进奉状》),里面说,高丽数年不至,许多地方的百姓都照国策办理,没有跟高丽来往,只有“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其间凶险之人,犹敢交通引恶,以希厚利……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
苏轼说的徐戬,正是泉州商人,按照东坡先生所列的“罪状”,他收受高丽财物,在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板2900多斤,“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说起来,还对雕版印刷和经籍在朝鲜半岛流传作出了贡献呢。
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此后,泉州与广南东路市舶司和两浙路市舶司并称三路市舶司。到了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朝廷发“空名度牒”给三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钱”时,广南和福建各五百道,两浙则是三百道,可见当时泉州已经和广州并驾齐驱。
地利之便,市舶之利
南宋时期,远离兵火的福建成为南宋王朝的大后方。建炎初,金兵南下的时候,宋朝宗室中两大宗支——南外宗正司和西外宗正司分别迁到泉州和福州。这些人对金银香料犀角象牙等舶来品的追求,自然也推高了泉州的进口贸易。
更重要的是,只剩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大不如北宋,对于海外贸易更加着力。宋高宗就认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所以绍兴六年(1136年),知泉州的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并提到“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者,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简单说,就是能够招揽海外商人来的,补官;主管市舶的官员抽买乳香每到一百万两的,升官,能够招商出海到国外的,回来也升官。
这个政策一出,自然有人响应。泉州蕃船纲首蔡景芳,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四年,招诱贩到物货,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补承信郎。到绍兴末年,泉州市舶司一年的收入据说可以达到100万贯。
由于南宋的首都在临安(杭州),从广州上供的货物到临安需要六个月,而泉州只需要三个月。这种地理优势也推动了泉州的海外贸易。
那个时期泉州海外贸易发展迅猛,许多海外商人到此贸易。成书于南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年)的《云麓漫钞》里就有一条“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船舶”,里面详细列举了来泉州贸易的海外船舶,有大食、嘉令、麻辣、新条、三佛齐等31“国”,除了阿拉伯和高丽,不少地名是今天东南亚一带的古代文明。
后来担任泉州市舶司长官的赵汝适写了一本《诸蕃志》,依照他的记载,当时与泉州直接有往来的国家或地区有58个之多。曾经担任过主管官员,又多和商人交流,他的记载自然可信度极高。
“世界上最大的港口”
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一位富商打破惯例,被委任为泉州市舶使。就南宋来说,这是市舶司前所未有的事情:不仅起用商人,而且还起用一位外国人。
这位名叫蒲寿庚的人,担任市舶司的时间尽管不长,但此后掌握了福建海上力量,并专擅福建海外贸易,直至元初。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研究这位《元史》没有专门传记的人物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泉州在中外交通史上的地位。——1923年,日本学者桑原陟藏出版了《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事迹》,首先指出宋元以来屡次见于外国人记载的Zeyton或Zaitun是“刺桐”的音译。到1926年,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名家张星烺到泉州考察,写了《泉州访古记》。此后,中外史家一致认定,刺桐就是泉州。而泉州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也由此为世界所知。
与宋代相比,元代对于私人贸易比较鼓励。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发布法令,由官方给予官船和本钱,选人出海贸易,官取七成,私人占三成。尽管带有官方垄断的色彩,但是这也给私人海商的发展提供了借助官方力量的机会。
1347年,摩洛哥旅行家伊宾·拔都他经海路来到泉州,他见到的景象是大船百余、小船不可数,他盛赞这里是天然良港,并且还称赞这里生产的绸缎品质优良,这里出口的瓷器,甚至远达自己的家乡摩洛哥。他的总结是,就算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也不过分。
就在他到泉州之前17年,1330年,一位叫汪大渊的江西人,从泉州跟随海船出洋,这一年他20岁。5年之后,他返回泉州,并在1337年—1339年第二次出洋。又过了十年,1349年,泉州路的长官偰玉立要编修一本《泉州路清源志》,鉴于泉州海外交通之盛,想着记上一笔。于是,他便请来亲身游历诸国的汪大渊执笔,这便是《岛夷志略》。
依照《岛夷志略》,元代与泉州有海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除了澎湖和琉球外,有97个,输出的商品虽然以福建出产的为主,但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商品。
其中尤其是泉州产的“泉锻”,驰名海外,伊本·拔都他就说,1340年元朝遣使往印度,赠送其国王锦缎五百疋,其中有一百疋就产自刺桐城。而张星烺则认为,英语、法语、德语中的“缎子”(Satin)一词就是源自阿拉伯语“Zaytūni”(刺桐)一词。
中国的瓷器也是当时泉州出口的著名商品。德化屈斗宫出土的高足杯、粉盒、军持等许多瓷器,都曾在印度尼西亚、日本、菲律宾等地发现过。
“生齿无虑五十万”的大都会
宋元时期泉州的海外交通,大致有几条路线:
从泉州启航,经过中国的西沙群岛(万里石塘)可以到占城,也就是今天越南南部。宋代洪迈的笔记小说《夷坚志》,就有一个故事说,泉州人王元懋随船到占城,侨居十年。
到达占城后,海船从这里还可以前往三佛齐(今天苏门答腊的旧港)、勃泥(今天加里曼丹岛东北)、爪哇等。1957年,在莆田发现祥应庙碑记,上面记录了泉州纲首朱纺前往三佛齐时,曾经来庙请“香火”,“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不到一年,获利百倍。
从泉州启航,经过南海、三佛齐,越过马六甲海峡,可以抵达印度,从这里换乘小船前往波斯湾。从波斯湾又可以沿阿拉伯海岸西南一直到亚丁湾和东非沿岸。按照《宋史》的记载,这条航线单程顺风也要160天,往返一趟需要大约2年。汪大渊就曾经到过东非的层摇罗,也就是今天的桑给巴尔。1888年曾经在桑给巴尔出土过宋钱和宋瓷,证实了史籍的记载不虚。
从泉州,还可以经占城、绕道勃泥前往麻逸、三屿,这些地区都位于今天的菲律宾。
前往南洋以及阿拉伯的各条航线,一般都是每年冬季趁北风出海,第二年夏季趁南风返程。此外泉州还有沿东海而上,前往高丽,也就是今天朝鲜半岛的航线,这条航线则是每年夏天出发,冬季返程。
在当时,经泉州输出的商品,主要是瓷器、丝绸等,而输入的商品中,香料以及各种宝货占了很大部分。
宋代福建的造船技术十分先进,“海船以福建为上”的记载屡见于宋人,南宋时期,泉州的水军还常常被调去防备海盗和金人。而泉州出土的宋代大船,也印证了史籍的记载。2010年11月15日,泉州的“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泉州的城市人口也大量增长,在北宋元丰年间泉州人口已经达到20万户以上,当时全国达到这个数字的州郡还是少数,而到南宋末年,户数一度达到25万以上,算上在此居住的外国人,有记载甚至说“生齿无虑五十万”。
泉州的公共事业也日渐发展。最集中反映这一点的就是泉州的宋代古桥,由此也可以窥见当时水陆运输的繁盛。这其中,最有名的如由蔡襄主持的洛阳桥,修建于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还有晋江安海的安平桥,修建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是当时全国最长的桥。
泉州城南,靠近晋江,便于出海,也由此成为商贾和外国人的聚集地。唐宋时期的“蕃坊”就在这里,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郡守在城池南门外扩建翼城,将城南纳入城中。
泉州衰落,但泉州人才刚刚登上舞台
泉州的好日子在明初结束。那时的世界,也正站在一场大变局的关口。
在那个年代,欧洲商队要航海前往东方,只能仰赖威尼斯人,从威尼斯到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然后从这里经过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地盘,再到印度、东南亚,最后到达中国。尽管海路成本远比陆路便宜,但架不住中间经过的势力太多,“中间商赚差价”的尴尬始终少不了。而在此时,奥斯曼帝国正在崛起,崛起的奥斯曼试图垄断商路的利润,而在欧洲,葡萄牙也即将开始寻找直接通往东方的海路,摆脱中间人,直接与东方文明打交道。
大航海时代即将开始,然而泉州本身并没有赶上这个时代。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义兵万户赛甫丁和阿迷里丁据泉州叛乱。所谓的“义兵”,是元朝在南方武装力量不足的背景下号召各地成立的、对抗农民起义的武装。仅仅几年之后,1363年,在泉州主管诸蕃互市的那兀纳也发动叛乱,这些色目人相互攻杀,波及福建许多地方。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陈友定攻入泉州,叛乱才被平定。这场延续十多年的叛乱,让泉州的经济遭遇了很大的破坏。
明朝成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厉行海禁。这也标志着,明朝开始扭转唐宋以来在对外关系上重贸易而不重朝贡的倾向,由此,朝贡体系成为明朝对外关系的重点。在这样的着眼点下,重新在泉州设立的市舶司不再以贸易为重心,其工作对象也主要变成今天日本冲绳县的琉球。
泉州是一个河口港,这也注定了沧海桑田对港口的影响太大。随着泥沙不断在出海口堆积,宋元时期繁荣兴盛的后渚港,到了明朝已经渐渐淤塞。天然良港的条件此时也已不再。
种种因素,让“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成为过去时。泉州也因此由宋元时期人口密集转为“城大而土旷”的城市。
不过,泉州人并没有退出海洋这个舞台。
北宋时,泉州惠安人谢履写过一首《泉南歌》,其中有几句保存在祝穆的《方舆胜览》里:“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这首诗道出了泉州的现实状况:正是“人稠山谷瘠”使得“每岁造舟通异域”成为更好的选择。
这种情况到了明朝并没有改善。在明清时代,泉州山区虽然有一两个县粮食较多,比如安溪县“其谷足以食郡中”,但绝大部分地区与沿海一样地少粮缺。乾隆《泉州府志》录《温陵旧事》一书曰“( 泉州) 山县田于亩者十三,田于山者十七,岁入谷少,而人浮于食”。
耕地少这个现实,让泉州人无法安心种田,只能向海而行,去种“海田”。
这也直接促成了安海以及安平商人的崛起。
安海港位于围头湾内,港口有白沙、石井两个澳对峙形成海门,过了海门就是一片平静的水域,而且也有避风的船坞。海船从广州到泉州,最先抵达就是安海,然后由这里转向北面的后渚港,从围头湾到后渚港的这段海路并不平静,经常有横风、逆流,相比之下,围头湾内风平浪静更加吸引海船。更何况,与后渚相比,这里离治所比较远,官府的管制没那么强,明代人就说这里“县治去远,刁豪便于为奸”,私人海商比较容易在这里集聚。明代末期,著名的海商兼海盗、也是泉州南安人的郑芝龙,据点就在安海,而他的儿子郑成功,在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以前,也是将这里当作基地。
随着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的落脚,东南亚逐渐取代波斯湾,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在这个舞台上,泉州人依然有自己的地位。如果说此前的泉州,在商贸领域唱主角的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那么此后泉州人开始唱主角。
著名的历史学家傅衣凌在游学美国时,读书于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图书馆,在馆中获见晋江人李光缙的《景壁集》和何乔远的《镜山全集》两书,写出了《明代泉州安平商人论略》,所论述的主体就是明代安海的商人。
也正是傅衣凌先生,较早指出,清代广东十三行行商中的潘同文、伍怡和、叶义成、潘丽泉、谢东裕、黎资元诸行,其先皆为闽籍,而其中又有不少泉藉。
泉州数百年“开洋通番”的历史,换了舞台,一样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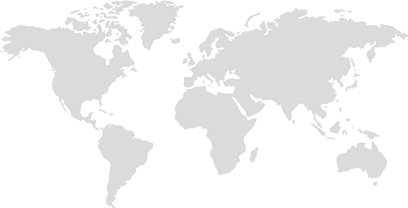






 汽车
汽车




 电话:0591-87851720
电话:0591-87851720
 传真:0591-87851720
传真:0591-87851720
 邮箱:minswx@163.com
邮箱:minswx@163.com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数字内容产业园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数字内容产业园
 法律顾问:福建宏飞律师事务所 吴跃华 主任律师
法律顾问:福建宏飞律师事务所 吴跃华 主任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