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两天白天在档案馆继续抄建国初期的档案,晚上在写郭永怀的稿子。其实也写不出什么新东西,全是二手的资料。只是不由开始揣摩起李佩的心境,钱学森说郭永怀“一方面是非常冷静、严肃的科学态度,另一方面又是火一样的献身精神,是冷和热的结合。”,能和郭永怀结为伉俪,大抵李佩也是类似的性格。用一本书名来形容的话,《巨流河》大抵是不差的。
1968年,李佩50岁,永远地失去了她的爱人。宣传中,郭永怀和警卫员牟卫东紧紧地抱在一起,胸前的绝密文件完好无损。真正留给李佩的只有半副眼镜和一个烧焦的公文包,当时李佩在中科大(彼时仍在北京)被抓进牛棚,郭永怀从力学所同事那辗转得知了这一消息,12月4日打过电话5日就上了飞机。实际上,如果郭永怀回北京不是为了汇报工作的话,那么带着绝密文件就很可疑了。
处理完郭永怀的后事,李佩仍然在单位接受审查,初中毕业的郭芹自愿回到吉林白城插队的地方。李佩1970年初随中国科大迁到了合肥,留下因生病在家休养的郭芹一人在京,这或许也为她的早逝埋下了隐患。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李佩离开中科大之后再叶不愿意回去,直到她决定把两弹一星奖章捐给中科大。
之前我一直相信了新闻宣传的说法,也相信李佩在力学所给郭永怀塑雕塑时坚持把郭永怀和牟卫东放在一起,让他们两个永不分开。但是我越想越不对劲,杨振宁回国看望邓稼先的时候,问过邓发了多少奖金,邓夫人说只有10元,邓笑着接话,20呢,原子弹10元氢弹还有10元呢。说明他们都看得很轻,但这不足以说明李佩为此专门回了一趟中科大,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反讽和伏笔。正如她坚持把郭永怀和牟卫东的骨灰放在一起一样,她只是想说明郭的死和牟有关系,而她下半辈子都在追寻飞机失事的真相,却一直没有答案。
今年她已经98了,也许她等不到这个答案,可能我们都等不到。
二、
我正在为这个猜测而犹豫要不要联系李佩先生的时候,知道了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铺天盖地的消息让人眼花缭乱,好像那些之前从不读书的人一夜之间都生长了起来,让我感觉自己读书真的太少,大隐隐于市,人家读书从来不显露,只在作者去世的时候才说一句,您老的书我读了一辈子。虽然作者早就听不到了,也不知道是说给谁听。
杨绛的书我只读过一本《我们仨》,还算有趣。而且和李佩特别像,丈夫,儿女先后离世,孤家寡人,一个人面对繁杂的世界和时代的洪流。
当然,杨绛是极爱钱钟书的,每一本传记面世她都要一一过目。王小波餐桌上经常编排一位丁部长,据说杨绛就经常给丁部长打电话,哭诉某某书写钱钟书写的不对,那些书后来就再也看不到了。这自然是恶意的夸张。
我没办法判断这么做的对错。从法律上讲,有人侵害了自己亲人的名誉或隐私,应该通过正规法律途径才对。从历史角度说,口述史的当事人讲的也未必是真的,杨绛眼中的钱钟书可能是最可爱,最傻气,最天才的,然而历史就得把他扒光了看,老人家未必受得了。
我也就明白,问李佩先生也不那么重要了。李佩说郭永怀是回来看她的,但两弹一星本就是保密的,谁知道郭是不是另有任务呢,或者本就有双重目的呢。至于那些猜测,本就是臆断,客观条件并不允许,就让它成为一个小说演绎好了。历史是当代史的意思是,现在有条件做的历史总是掺杂着当代人的社会思潮。
何况,通过渠道得知,没有办法采访到她,哪怕我说只要远远看一眼李佩就好。说完这句话,我自己都被吓住了。这么温柔的情话本该用在亲人或爱人身上,我却用在被研究的对象身上,我也就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为了一个历史事实或人物争论不休,哪怕同一个证据,也会有不同解读。
观察本就渗透理论,喜欢了就自然要替她辩护,就好像在为自己辩护。
三、
杨绛比李佩幸运的地方在于,她知道怎么用文字替“我们仨”辩护,我们才能了解他们更多一些。
不可否认的是,我很喜欢杨绛的家庭氛围。比如杨绛说,她和钱钟书最喜欢的是宝物是隐身衣,我每次想到这个场景就会感觉极度的浪漫,仿佛世界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人打扰,他们的时间和外界是不同步的,哪怕胸前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两个人都能互相揶揄,相视一笑。
李佩就不幸的多,郭永怀回国就自动隐身,没有人知道他。这个本来学光学的摄影少年和大多数少年一样在西南联大转向了更实用的领域——航天工程,今天看来林徽因的《哭三弟恒》似乎也成了郭永怀的注脚:“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而千万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小时候我对隐士特别的不解,为什么能归隐的必须先爆得大名,大概普通人是没有权力隐身或者归隐的吧,大家就像陌生的全同粒子,并没有什么区别,路人甲和路人乙对于我来说其实都是一样的。毕竟,每个人都只过他自己的生活。
当然这种平等,某种意义上在那个年代也实现了,大家穿一样的制服,吃一样的大锅饭,做一样的工作,好像每个人都是灰色背景里的一个像素,衬托着红太阳的光芒万丈。
历史大概还是永远属于英雄的吧,毕竟故事好看才能流传下去。
到今天,我们的生活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成为英雄的方式发生了一些改变。“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的真实情况必然是英雄遇上美人,不然就变成两个普通的农夫农妇,大家就会嫌弃这个故事太没有格调。
四、
我之前从来没有从李佩或者杨绛的角度想过一个人看到自己的挚爱化成了灰是什么感觉,后来想起了几个细节。一是外祖父去世的时候,我赶回去,母亲看到我就不停地流眼泪,抱着我说:“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想起庄公“尔有母遗繄我独无!”,伤感愈甚。而外祖母则一直追着灵车,呼喊着他的名字,想和他同去,又被大家拦住。
一是在曾祖父的文集中看到一篇《给亡妻信》,开篇是:「我總以為你的精神沒死,還活在世上了所以三番五次給你信,你收閱了吧!慰問你就是遣消我的悲哀!」以致看着身上的衣物,没一件不是曾祖母缝补的,不由嚎啕大哭。又某日,「仿佛在門口掃垃圾,忽聞說話聲,回頭看去,見你站在房門口,玉容含笑,好像五十歲形狀,我問你同誰說話,你答:“我同自己說”即便驚起!思你更加難過。“我和自己說話”者,可憐我今日無法和你說話,其苦情和我今日無人說話一樣。」
大概就是一个人掉进黑洞的感觉,世界人很多,却不屑、不想、不愿与他们交谈,而能说话的人却再也看不到了。都说要做果壳里的王,如果整个世界只有孑然一人,倒也不坏,万幸的是遇到一个可以待在一个隐身衣下的人,最不幸就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连虚拟的宝玉闻罢抓起那劳什子往地上砸,“如今来了个天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后来发现原是有的,这筵席也就散了,泪也就流尽了。
也就不免赞赏林黛玉既然要散,何必相聚,有趣的人儿也必终将互相嫌弃。
君子慎独,却不免感慨和渴望遇到一个和自己一样被世界遗忘的人,比如司马牛“人皆有兄弟而我独亡”,屈原“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今天那些冒出来的一大茬的未亡人,大概也能成为好朋友吧。
热闹是你们的,我依旧什么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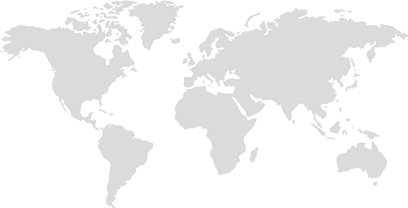






 汽车
汽车




 电话:0591-87851720
电话:0591-87851720
 传真:0591-87851720
传真:0591-87851720
 邮箱:minswx@163.com
邮箱:minswx@163.com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数字内容产业园
地址:福州市晋安区数字内容产业园
 法律顾问:福建宏飞律师事务所 吴跃华 主任律师
法律顾问:福建宏飞律师事务所 吴跃华 主任律师
